爱不再是勇敢的冒险,而是一种精心计算|格非、汪民安对谈

最近,作家、清华大学教授格非,与知名学者、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民安,B站读书UP主、文学编辑渡边共同参加了一场名为"寻找城市选书人"的活动,一起聊了聊有关生活、爱、写作与哲学的事情。
分享会从汪民安的新书《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开始聊起,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讲到了友谊,古典友谊的核心,是要两个人共处。但到了今天,友谊的定义恰恰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法国作家布朗肖说,“友谊是要保持距离。友谊不是在一起相处,友谊恰恰是应该不见面。”
顺着友谊,随后又聊到了爱情。汪民安说,在当下人的爱情观里,“爱不再是勇敢的冒险,而是一种精心计算”。构成爱的原始核心——情感,或者激情,在当下的人心里已经一点点衰减,成为了某种奢侈品。
格非在新书《登春台》中也写到了爱情的主题,格非说,“现在有两件事情能让人获得幸福感,一个是爱情,另外一个是投入到工作中。”这与我们看待工作的态度极为不同,为此,他们区分出被动劳动与主动劳动。汪民安说,“被动劳动是不会幸福的。”
以下为渡边、格非、汪民安在分享会现场的对谈实录,篇幅所限,内容有删减。

分享会现场图,左起:渡边、格非、汪民安
#01
“人和动物的差别在于,人是有友谊的动物”
主持人(渡边):今天汪老师这本书叫做《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我们不妨就从友谊开始聊吧。
汪民安:古人对友谊是非常推崇,我记得培根就讲过这样的话,人和动物的差别在于人是有友谊的动物。我原来经常听到各种各样的人和动物的区分,人是语言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我第一次听到人是友谊的动物,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提法。
友谊到底什么是友谊?在古典时期,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讲到了友谊,友谊很核心的一点,要两个人共处。还有友谊中实际上两个人彼此相似,真正的朋友是另一个自己,这是亚里士多德另外一个观点,我们对待朋友就像对待自己一样,这是非常核心的,还有两个人要相似,朋友是合二为一的,这是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论述,一直影响罗马时期的西塞罗、蒙田,在欧洲一直有一个友谊中彼此相似,一个朋友是另一个自己的传统。
到了20世纪有一个法国作家非常有意思——布朗肖,他的书在中国也有一些出版,非常特殊的一个作家,也是一个哲学家,在哲学和文学之间,他提的一个概念,跟以前的友谊观念完全不一样的,他说友谊是要保持距离。友谊不是在一起相处,友谊恰恰是应该不见面。
什么是不见面的友谊?真正的朋友有一种是知识上的友谊,我从来不见他,我不说跟他是朋友,甚至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内心把他当朋友,在另外一个方面他也会把我当朋友。真正的朋友是知识上的朋友,我们彼此看对方的书,彼此互相欣赏彼此有一种心理上的默契,但是从来不见面,这个友谊跟以前讲的欧洲的古典传统讲的友谊不一样,古典讲的友谊要见面要相处,不见面不相处,哪怕最好的朋友关系也会淡化,而且最重要的是友谊要两个人重叠,两个人要彼此有绝对的一种默契和相似,但是布朗肖把这两点去除了,可以完全不一样,可以保持距离,可以不见面。

《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
汪民安 著/ 重光relire、艺文志eons 出品/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24-5
格非:关于友谊我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布朗肖的说法,友谊是不是一定要维持?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维持两个人之间的友谊那种交往,去预热它,或者去培养培植,这个非常辛苦。
我的那些朋友大部分到了北京以后,会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说我来了,我听到后脑子里嗡了一下,“我来”的意思是你得来见我,还有一些朋友喝酒喝到一半的时候想起我,打电话说,来喝酒。我一开始是会无条件去的,后来我下决心不去了,这个当中我觉得有一种道德上、一般的礼俗人际交往上的很大的困惑。我完全同意汪民安老师刚刚引用的布朗肖的观点,两个人之间的友谊,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
我在北京跟很多很好的朋友,一直不见面,每年都会打电话约,但是双方都有事情,有时拖着拖着可能十年没有见面,有时候可能在一个场合见面了。但我们会经常发微信,看到好的文章会彼此推荐,好的书花钱给我寄过来,这是非常好的朋友。我要说的友谊的第一点,今天的社会,跟乡村社会的友谊的状况完全不同,布朗肖可能也是基于社会的巨大的变革,提出这个,我觉得非常必要。
第二个友谊这个东西能不能把它延续到,比如异性。有人觉得男人之间可以有友谊,但是男人跟女人之间呢?我很早以前在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跟女士能够保持一种心灵上的沟通,精神上的非常好的默契度,这个东西也是我特别向往的,我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汪老师的书里面也提到,所有这些地方我们有高度的默契度的。
#02
“爱不再是勇敢的冒险,而是一种精心计算”
主持人:接下来我想请问两位老师,如何看待友谊和爱情——我们作为人类共通的很重要的体验之间的异同呢?汪老师有一本书《论爱欲》,这方面肯定是很有发言权的。
汪民安:蒙田有一篇文章讲过友谊和爱情的区别,他说爱情像火焰一样,会非常激烈地燃烧,会让人受不了,很容易到顶点。一旦是相爱的时候会对对方有全部的了解,两个人有非常深的接触,了解对方的一切,甚至了解对方的身体,了解对方所有的最秘密的深处。一旦你把对象一切的秘密了解之后,通过爱情,某种意义上也是婚姻,你的那种新鲜感或者你的求知欲,或者好奇心也可能会消失殆尽,然后是爱情的火焰烧到顶点之后是慢慢的熄灭,反而有可能变得越来越远了,它有一个高潮和低谷。
友谊和爱情方面是有点差别的,友谊你永远不可能关系烧到顶点,友谊是有温度的,比较温暖,一直总是有点距离的,两个朋友之间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绝对的对对方的彻底的了解,某种意义上你不可能有一种好奇心完全的满足,友谊永远是在一个探索对方和接近对方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因为友谊不可能完全了解,总是有一些未知的部分,它会保持更久远的时间,更稳定,也可能更平静,但是它不容易消灭。
他还讲过一点,蒙田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跟以前的古典社会完全不一样。他说当你爱一个人时候想到有一天会恨他,恨一个人的时候想到有一天会爱他,但是友谊不会,哪怕感情有一天会破裂的时候,你可能会讨厌他,或者会瞧不起他,但不一定会恨他。爱可能会导致恨,但是友谊破裂了不会导致恨,分手了也有这种差异。
主持人:格非老师在文学作品当中也是经常以爱情为主题,您曾经说现代小说中的爱情大多是非典型的未完成的,在您创作当中如何通过小说里面的人物或者情节来反映这种情感模式的?
格非:我觉得对我来说,情感这个概念是特别复杂的。从理智的角度来说,当我们说一个事情发生了,我们要理智的来对待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往往是很滞后的,首先做出反应的一定是身体,也就是说,一个事情发生了,我们马上作用,我们马上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情绪是首先到达的,你首先还没来得及考虑清楚这个事情是什么的时候,情绪已经开始抵达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发现情感这个问题要比我们后来说的理智要宽广的多,理智就是趋利避害,这个事情我能不能做,损失有多大,大到那个人要不要退让。

格非
但是情感这个东西非常复杂,有情绪,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总的看法,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总体情感是逐渐衰减的,一步一步的衰减,在我们今天情感已经成为奢侈品,我们可以付出金钱,付出时间,付出耐心,但是唯独不能付出感情,因为我们感情都已经没了,被耗尽了。一个人感情被耗尽,今天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社会从各个层面对我们进行管理,来告诉你该怎么做不能怎么做,对一个人动怒也不能打他骂他,这样的制度管理之下,也由于劳动分工的细密化,情感越来越趋向于衰竭,这是我的总体的看法。
你说到的非典型的爱情,小说里面写到的,刚才汪老师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想到,我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我说过这样的话,文学作品里面所有的爱情都是非典型的,比如大家看过《安娜·卡列尼娜》,里面的弗朗斯基跟安娜的情感就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激情,不是一般的情感,它是激情,这个激情不等同于全部都是爱情,有的时候也有其他的激情。爱情一定是一种激情,一定是燃烧的。
我记得穆齐尔写一个男人喜欢上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同时也喜欢他,那个女人是有夫之妇,两个人坐在草地上聊天的时候突然觉得两个人产生了那种激情,不是一般的爱意,他的小说里面有一句话描述当时的爱情发生的空前激烈的状况,他说他们两个人的膝盖都在燃烧,非常厉害,非常强烈的那种情感。
当然,我觉得文学作品里面还有一种情感特别重要,非典型的,就是大部分爱情都是不能实现的。不是说一个人一定要谈成恋爱才能成家立业,成为夫妻,不是,文学作品里面大部分是没有办法达成的。
我们小时候有的时候在乡村社会里边,大部分你爱慕一个女子都是单相思,这在我和汪老师童年时期和青年时期很普遍,今天的社会谈恋爱的时候状态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我跟清华同学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谈恋爱很简单,你怎么样,我怎么样,表白一下,很清楚,不行就拉倒,换一个人再试,很清晰。
这种东西我觉得社会也在发生变化,我一年上课给同学们推荐纪德《窄门》,下课以后一大帮同学问这个小说写的什么意思,我说难道你们已经开始读不懂这个作品了吗?后来我想想可能真的读不懂,他对于情感的变化,他很难理解纪德笔下的那种情感,没有实现的情感为何如此强烈,这个都是我觉得时代变化所导致的。
主持人:现在年轻人都会去计算我要不要投入到这场爱情之中,我跟别人谈恋爱能得到什么,有哪些风险,就算做投资一样,这部分汪老师的书里面也有提到,这篇叫爱不再是勇敢的冒险,而是一种精心计算,这导致很多人害怕失去,害怕损失,而不敢去爱,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汪民安:实际上把人类几千年文明了解一下,真正的自由恋爱的历史非常短的,在中国的也就是20世纪开始,也是学西方的。
西方自由恋爱的历史是从浪漫主义开始的,在19世纪,在个人主义或者启蒙运动之后,在这之前人类基本上没有男男女女自由恋爱的历史,大概也就是一百多年。为什么会出现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情况,以前,可以说是在启蒙运动之前,基本上男女如果真的是因为激情,两个人完全情感的碰撞所产生的感情,大部分都是未完成的。
如果在那种情况下你想把它完成的话,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能的,就可能出现罗密欧和朱丽叶这样的悲剧。古典时代所谓的自由恋爱都是一种冒险,只是说到了19世纪浪漫爱、罗曼蒂克出现之后,自由恋爱才是有可能实现的,这个历史非常短,在中国也是非常短暂的历史。
在今天看上去好像是可以自由恋爱了,今天年轻人在一起随便自己愿意选择对象,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也不是完全的自由选择,还是有一种世俗考量。虽然一方看上去是自由选择,两个人不需要家族干预,也不需要社会干预、权力干预,但是他们自己就会衡量,婚姻和恋爱也变成一种投资,是投资和收益的行为。
我跟他恋爱是一个投资,或者定了一个合同,我觉得也是最近半个世纪在西方开始出现的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模式,把一切人类的活动理解成为经济活动。

汪民安
美国在70年代出现了一批经济学家,他们特别强调开始重新把人的所有的行为活动都理解成经济的投资,都是要获得收益的,爱情和婚姻都不例外。当时出现经济学帝国主义,解释一切现象,包括养孩子,母亲抚养孩子,是一个规律主义行为,经济学家解释养孩子可以不求孩子的回报,可以不求孩子长大孝顺你、扶养你。
但是在中国一直有一个传统的,养孩子就是为了防老,这是一个经济行为,即便我们现在不再有这么一个观念,经济学家还是说养孩子虽然不求他回报抚养你,但是你把孩子抚养好的时候也会得到收益,也会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也是你抚养孩子投资的一个回报,一切行为都可以理解成投资和收益的这么一个事情。在今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爱情,某种意义上婚姻就是一个市场,就是一个权衡。
一方面看起来好像我们是在自由恋爱,好像我们可以任意选择对象,另外一个方面市场法则,市场交换法则还是在主导着我们的选择,是主动的,但不是完全主动,还是听命于某种市场法则,决定的婚姻的法则,我们现在是不是模仿,当然是模仿,如果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我也会这么考虑。
很多人实际上是不会谈恋爱的,包括现在一些婚恋节目,都在教很多年轻人怎么谈恋爱,现在网络上各种各样的恋爱指南、恋爱课都是在教,但是教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说都有一套模式,是遵循市场模式的。
主持人:你怎么看待这种模式的恋爱?教你一种方法谈恋爱,有一个人按照一个秘籍一样地讨好一个女孩或跟一个男孩相处,你认同这种模式吗?
汪民安:我肯定是不认同,但是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很难有一个合适的方式,像真正的浪漫之爱,我们说罗密欧、朱丽叶这样的爱,从爱情本身来说,从个人的激情来说当然应该是值得去激励和夸张的,某种意义上也是满足人性要求的手段,但是反过来,它在那个时代会遭到毁灭,是未完成的。
刚才格非老师讲到人的感情在变淡,我也非常赞同。格非老师《登春台》小说里面表现的比较明显,我特别喜欢是第二章的静熹那个女性形象,她非常冷静,最后她离开也不是说要大张旗鼓地离开,就是默默地离开,非常理性地离开。她对那个男人一开始肯定是有爱情,慢慢离开,情感的折磨,她的收敛,变得冷静,计算,非常清晰的,绝对不是古典爱情当中的分手的那种爆炸式的事件性的。
#03
“我觉得当代人是不配有命运的”
主持人:格非老师这次也是带来新作长篇《登春台》,小说叙写了80年代到现在40多年,采取了四段式的叙事,看似没有联系,好像又有一条隐秘的暗线相连,最初怎么想到以这样的方式来创作这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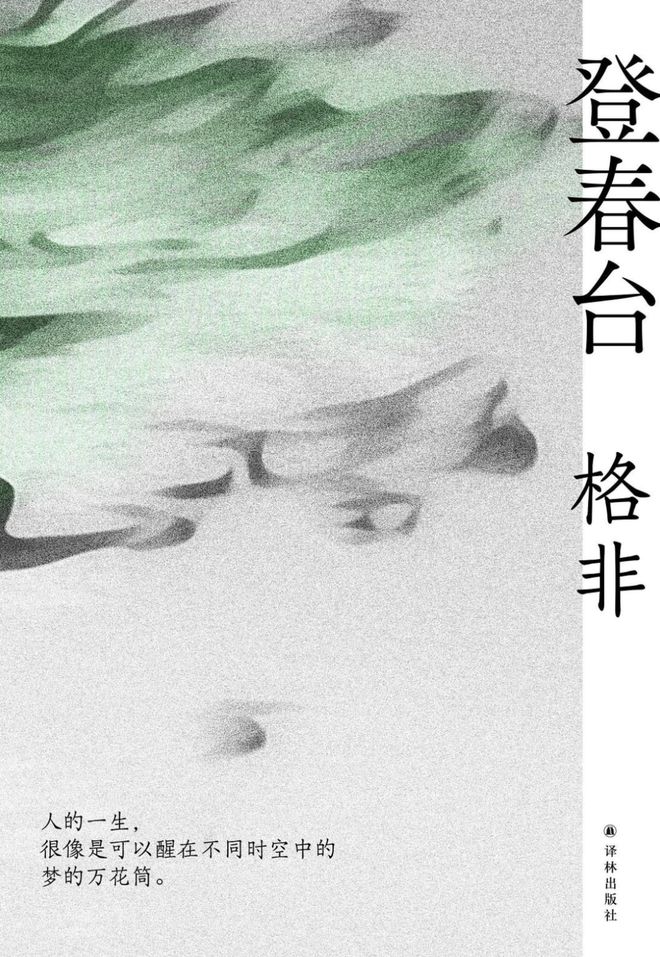
《登春台》
格非 著/ 译林出版社 出版/ 2024-3
格非:在刚开始构思这个小说的时候,是发现如果把一个人的命运从头写到尾,持续很长一个时间,我觉得已经很难表达我对当下生活的当下性的理解。
我觉得当代人是不配有命运的,将来多少年所有的事情你都知道,那种起承转合写人的命运的波诡云谲、跌宕起伏,虚构的浪漫主义的传奇,我早就厌倦了。我觉得必须重新来思考命运,比如如果说我们当下还有命运的话,这个命运是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出现,这样的话会考虑不同地方的不同的人物,这个当中让他们建立某种联系性。
主持人:格非老师说过一句话,说现在有两件事情能让人获得幸福感,一个是我们刚才谈论的爱情,爱别人和被别人爱。另外一件事情是投入到工作当中。
在汪老师这本书也谈到了工作、劳动,提到了把劳动分为两种,一种是主动的劳动,一种是被动的劳动,主动的劳动可能是我们自己去开创创造,被动劳动可能是我和台下大多数朋友的被雇佣的劳动,这种劳动我猜很多人都会有一些共同的情绪,它好像被一个轮子赶着一样,产生日复一日的重复,产生一些倦怠之感。
问一下两位老师现在如何看待年轻人产生的普遍的倦怠,有没有一些突破点,有没有办法解决它,或者有没有一个办法帮大家在疲惫工作当中有喘息的机会?
汪民安:大部分人还是被动劳动,投入到打工或者帮别人干活我觉得是不会有幸福的。工业主义时代之后,劳动基本就变成了一个苦力劳动,要适应机器。卓别林的《摩登时代》中,人是机器的一个配件,马克思讲工人的手臂完全吻合机床的节奏,他们认为这种劳动称为现代奴隶。
这种劳动最后变成非常无能了,工业时代让劳动者变成一个被动的东西,最后变成了什么也不能,只能是碎片是适合式的配件的东西。
今天的劳动者还有点不一样,工业革命的时代劳动者让你什么都不能,你只能配合机器,但是今天要让你无所不能,什么都要干,必须干,什么都要会,不会老板会骂你是一个笨蛋。
我们在两个时期都是要求你劳动,一个让你变成笨蛋式的劳动,一个让你变成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必须干。不管是让你不能,还是让你无所不能,都是被动劳动。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许我们的人工智能,将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解决,这种所谓的苦力劳动或者被动劳动都能被机器所取代,如果那样的话,人不是失业了?人干吗?黑格尔很早讲过了,如果到了历史的某一个阶段,人就只从事艺术,只从事恋爱,劳动都交给机器去干,真正的人类最好的顶点时期,绝对理性的实现时刻的话,人就去从事艺术和恋爱。
格非:我们今天很多的劳动都是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因为你愿意做的事情很少。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大家读过《西西弗斯神话》,加缪是写了在一个很极端的情况下,哪怕它是被动的,哪怕它确实带来无尽的限制,无限重复、厌倦,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觉得工作带来的最大的重要性就是创造性,哪怕卡夫卡写《万里长城建造时》,哪怕你把工人对调一下,你今天在这个地方筑这个城,万里长城你看不到,你的成果见不到,你永远看到的只是局部,亿万里的长城怎么看到。卡夫卡也在试图跟加缪一样,回答我们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碰到不喜欢的工作我们怎么办?
卡夫卡本人的例子也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卡夫卡在保险公司的生活远不像我们想象的像在他小说里边那么恐惧,他有非常积极的一面,他始终在为工人能够不把手指弄伤,来改进机器,来改进保险制度的赔偿。站在工人的角度,他推进了好几项法案的实施。我觉得卡夫卡这样把这个世界理解为一种荒诞的作家,也试图在里面找到东西。
主持人:格非老师在另外一本《月落荒寺》书里面写到,觉得他的整个读者群体换了一茬人了。两位老师在大学里面任教这么多年,见证了很多不同时代的青年的学生,对现代青年的学生有什么样的观察?现在跟十年或者二十年前比,这些学生有什么不一样的点吗?

现场活动图
格非:我当老师的时间非常早,我是1985年留校,我那个时候21岁,当年的暑假跟着带我的老师开始上写作课,我的岁数跟学生岁数差不多,我班上甚至有同学岁数比我大一岁,我跟学生混的很熟,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距离,他们对我很尊重,也会拍拍打打。之后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你从21岁到31岁几乎是一个年轻人,跟学生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
后来有一天我在课堂上提了一个特别愚蠢的问题,我说1981年的时候你们多大?学生哄堂大笑,他们都是90后出生的。我第一次尖锐地意识到自己老了。到00后的学生来的时候,他们比我儿子都小很多,这种情况下,我跟学生的距离感突然产生了,比如我要是看到有学生跟我谈什么恋爱问题,请教情感问题的时候,我立刻把这个任务交给助教,说你来,我不行,隔了一代人怎么知道人家怎么谈恋爱,谈恋爱的方式都不懂。我觉得跟学生之间年龄上的问题会造成一个交往上的问题,而涉及到文学,我们可以聊的很深。
第二个也是汪老师书里面提到的,我觉得现在很特别的学生很少,学生都差不多了,西班牙的哲学家加塞特说过一句名言,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存在第三种人,一种叫傻瓜,一种叫怪物,因为我们不愿意当傻瓜,所以我们拼命地想成为怪物,这是他对现代性的批判。我宁可自己怪一点,也不要被控制,你也不要被程序化,你要从程序里面逃逸出来,一定会有点怪的。
我觉得现在怪的学生比较少,大家都比较统一,都差不多,很可爱很聪明,特别的学生也是有的,不是没有,清华有一些学生很特别,这是我们当老师非常大的一个快乐,很多学生有很奇妙的想法,有的时候跟你聊天的会把你吓一跳。
主持人:汪老师你喜欢怪的学生吗?还是比较喜欢听话的学生?
汪民安:怪也有不同的怪,有一种怪人学生你很喜欢,有一种怪人学生很讨厌。我曾经碰到一个学生,他本科写的作业交给我,我当时一看,觉得这肯定是抄的,本科二年级的学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就让助教去查,结果助教说,老师,这个学生不是抄的,就是自己写的。
我当时非常惊讶的,我觉得他比我们所有的博士都写的好,后来他又来上了我一次课,第二学期后来又把作业交上来,我当时完全不怀疑他是抄的了,他比大多数教授都写的好。在清华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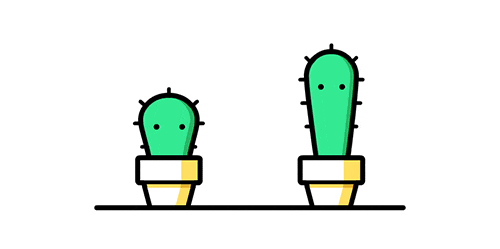
编辑 | 轻浊
主编 | 魏冰心
知识 | 思想 凤 凰 读 书 文学 | 趣味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