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天,要频频起身看风景
我们对远离城市、住进山里的生活充满遐想,却又很少真的实践。
今天分享的作家周慧不那么为人熟知,但被诗人黄灿然盛赞“她的语言更新了自己的感官,也更新了读者的感官”。周慧十八岁出门打工,通过成人高考上了大专,毕业后来到深圳,从事过形形色色的工作后,辞职搬到深圳东部山区洞背村居住了近十年。
她在四十岁开始写作,《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是她的第一本书。周慧住在一间三面有窗的房子里,这本书就是她从窗口眺望山和海、村庄和故人、远逝的青春和身在的中年,以及自己内心流转变化的坦诚记录。
本文摘选自周慧《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经出品方授权发布。
三月过日子
1
三月初的几天,窗外停满了雾,像一幅巨大的超现实油画嵌在墙上,没有图案,只有谜一样的哑白色。
屋被雾凌空托起。鸟、鸡鹅、工地的吊臂、穿着套鞋去摘菜的妇女、卖鱼佬的摩托车,各种声音穿上来,像穿过整夜巨型的梦一样,瓮声瓮气。
在屋里,想跟自己讲点话,也听不真切。
2
没有雾的时候,会觉得空气不对劲,像在密谋些什么,走到窗边看,雾正过来,先是几丝几缕,缠在树间,一动不动,过不久,大量的雾从山的缺口处涌来,滚动的一团团,淹没菜地、鸡舍、荔枝树冠、窗口。
所有的雾都从海上升起,海,已隐匿。
3
桥头有一座小山,孤零零一座,左右没有山和它连绵,植物都是风和鸟带来的,乱长一气。去年秋天,一大片荒草被锄掉,种上树,现在,雾散后,一簇簇明艳的黄花爆开在山间。
黄风铃开花时只有花,没有叶,花瓣从头到尾,正面反面,以及花苞都用一种颜色,闪耀而柔和的黄,凌空开在这只有原始低矮植被、人迹罕至的山上,不像是花朵在开放,像在宣誓。它原是巴西国花,现在,它像是在思念它的南美大地。

4
去葵涌,小巴走沿海公路,先是溪涌,大弯坡后是万科十七英里,整个海湾收入眼底,海面是一块块深浅不同的灰色疆域;上洞村,榕树冠后几幢残旧灰暗的屋顶;玫瑰海岸,有很多月季;油库,红色的油管长长地伸进海里;土洋,内有乾坤的偏安小国。太阳突然闪耀,海从灰变成蓝。
5
在粉店时,一个穿紫色外套的女人进来,说我可以坐在你这里吗?我说可以啊。店里只有一个女人在吃粉,还有四张桌子无人坐。她说,我觉得坐在一起吃得香一些。我笑。
我的螺蛳粉来了。她说,老板,我也要和她一模一样的。但我不知如何才能让她吃得香一些,她吃了几口,很快和过道另一边的女人说起话来。她的孩子是上中心幼儿园的,还有补贴。另一边的女人说,啊,你的命真好。
四月的第一天
四月的第一天,我坐在屋里,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哪扇窗下都坐不长,总是惦记另一边的山和雾,频频起身看另一扇窗,生怕错过一寸好光线。同一个方向的两座山,一座只比另一座后退一些,就被雾攀满了,而前一座山,清晰得像被神眷顾了一样。
雾、阳光、风,在春天做下的事远比其他季节多,怎么舍得只坐在一个地方?
冬天要好一些,冬天的天慢,任何地方都可以坐好久。有时阴一整天,就生炭火,看黑色的炭熊熊烧起来。
昨天下午去阳台看南方,正好看到几绺白色的烟在快速爬上一座山,看了一会,想肯定是山下着火了,而且是极大的火,否则烟不会这么快这么浓。
为了搞清楚是什么火,我打开门往楼顶天台上冲,一边冲一边想起鲁迅关于黑屋子起火的典故,第一个发现火的人振臂疾呼,喊醒全村人,还要喊醒菜园里的鸡鸭鹅,一些人醒来后往山上逃,一些人往山下跑,山下有海,一个猛子扎下去就得救了。
跑到天台,只见南边的山全被吞没,只剩山尖,白色的浓烟正迅速往上爬,没有一丝风,显然它们自己长了手脚。西边的山快沉没了,北边的毫不知情,还清晰地托着下午的阳光。
那烟雾,要淹没西边和北边的山,需要经过我,现在,它不动声色但迅疾地朝我扑来,我迎着,瞬间什么都看不清,随后鼻尖触到细如纱的水珠,原来不是烟,是雾。此时如果快速转身,还可以看到北边清晰的
山,慢一点的话,就什么都看不清了。之前对雾的印象停留在秋冬早上的田野里,平原的雾,来去都有迹有时,这里的雾比热带的植物还诡异。
一只鹰在雾里盘旋,它为什么不在起雾前吃饱?我准备在雾里奔跑,有人要我别在雾里跑,我还是往山里跑。就像一天里我要无数次起身去看其他方向的风景,一天里,也要起身出去两次,把脚踏在不同的泥土上。
往回跑时,一条长长的蛇横在路上,乌绿色,比墨绿更深,有一米来长,我在十几米远的地方停下,它漂亮得要命,眼睛黑亮,蛇嘴长长地印在颊边,小小的头娴静地立着。
我足足看了它几分钟,不知是想等它离开还是等它过来。我第一次勇敢地长久看着一条活着的蛇。往回跑时,我一直回头,看它有没有跟过来。
有朋友说,你一段路来来回回跑,会不会无聊?我想说,虽然只是一条路,但每天植物、光线、海湾、爬升的雾、盘旋的鹰都不一样,怎么看得尽?
我去过的地方不多,认识的人也不多,对世界有一些想象,但它们太遥远了,我连进城坐公交的钱都要挤一挤,遥远就成了真正的遥远,它们不比夜空的星星离我更近。
现在,我每天像蜜蜂一样从这扇窗飞到那扇窗,从这座山穿到那座山,在同样的时刻做同样的事。之前认识我的人慢慢忘记了我,我也慢慢想不起通讯录里的名字是什么样的脸孔,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我每天移动的坐标可以忽略不计,简直就像一株植物,四月的植物。我的世界,就是我的脚能踏到的地方。
五月的把戏
五月的温度好得闪闪发光,这时想变成一种植物,整日整夜待在这温度里。
不同的绿,深浅明暗的绿,到五月时渐渐统一,绿到深处各种花开,木荷、桃金娘、黄栀子、金花玉叶、黄牛木,每一朵花都美得具体而完整。
天气好一半坏一半,风、雨、雾都有,清早鸟叫得欢快。一年中最清脆的嗓音。潮湿的夜里,蛙声如牛叫。月亮经常被云层隐没,最圆的时候云也最多。
每天下午出村,下坡时,眼睛放平,越过树冠,树冠后是不远不近的山,山后的海露出一掌心那么多,海与天经常浑然一色。我是有次偶尔看到绿色的树冠上方有一窝湛蓝,而天空浅白,才发现那是海。
回村时,右侧的山逶迤俊秀,路与山之间是窄而深的溪峡,溪水奔涌,被树木掩盖,只听到水声却看不见,一条窄窄的锈迹斑斑的小铁桥穿过峡谷通往对面的山。通过去,但没有路。
树木葱茏诡异,遮蔽整个山体,树林里突然裸露出几块巨大的石头,没有人去过那里,也没有路可以去。我看着这山,假想是在陌生的地方,陌生的青翠的山,陌生的奔涌的溪,陌生的前方。
日子来到六月中
1
好天气时,减少睡眠,把时间让给清醒,去看云的耀洁、海蓝如黑、云影掠过北面最高的山,以及朗朗皓月。夏季最好的天气在六月,无法想象世界上其他地方有比这更好的天气。
白天我在房子三个不同方向的窗之间移动,傍晚去绿道,夜里在天台随月亮移动。
2
在老家,老二买了两斤青蛙,用菜籽油炒蜷后,加紫苏辣椒,很好吃,有母亲做菜的精髓。
她说:“记得小时候,睡到半夜,梦嘎梦醒的,她把我从床上拖起来,去照蛤蟆,我穿双套鞋,一条短裤子,打个赤膊,提着蛇皮袋,跟哒她去捉蛤蟆。”
“我怎么记得都是我跟她去捉的?”我说。
“你那时还小,提不动袋子,等你提得动的时候,才是你去的。”
田埂上的草拂到脚踝很痒,飞蚊跟着手电筒的光跑,萤火虫自己有光自己跑。蛤蟆被照到瞬间僵住,一动不动,母亲慢慢弯腰,出手迅疾,抓住反手往后递,我张开袋口,“嘭”一下,袋子轻微下沉,袋子里的蛤蟆一阵骚动。第二天中午,必定有一大碗炒青蛙,放紫苏青椒。

吃到最后,我和老二在碗底翻蛙腿肉,和当年一样,蛙腿肉和蒜瓣很像,吃到嘴里才发现夹错了。老二比我多吃两年母亲做的饭,她做菜比我更像我们的母亲。
3
六月过半,一年也过半,好天气与坏天气都来过,泉水也在上一场暴雨后涌出,村口的溪边小黄花长得及膝高,两个黑瘦男人拿着割草机呜呜割。刚下过几场暴雨,植物汁液饱满,草汁与溪边的泥浆乱溅,溅到脸上嘴上,他们歪开脸,嘴里扑扑吐泥星,整条溪谷弥漫着青草的香味。
七月梦寐以求
1
云从海上升起,一朵朵悬在低空,每一朵都有从耀眼的白到纯正的灰之间渐次的颜色,每一朵的边缘都各具形态,仿佛上升成云的水汽,有自己的喜好与低语。
白色的云徜徉的姿态,乌色的云暴烈,迅速升起,迅速移过来,有时从头顶上擦过,往背面的山攀去,有时整体压境,雨直接倒下来。
2
村口右侧山坡上,几场雨下来,银合欢像被天空拉长了,长得又快又密,山一夜间胖起来,有些已开花,白色的小圆球。
银合欢矮的时候不像树,有次看到一个男人探身看,凑上鼻子闻花,用手碰叶,碰完迅速将手收回身体一侧。我走过去说,这不是含羞草,这叫银合欢。他笑了,我说怎么不缩回去呢。
银合欢的嫩叶可做猪牛饲料,有微毒,但过量会导致厌食、生长迟缓、消瘦、繁殖机能减退。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食物啊。
3
方方正正一块空地,周围都是房,单它空着,几年里一直荒着,长着杂草、藤、几株木瓜。
后来草和藤都铲掉了,重新铺上草皮,种了两棵鸡蛋花树,一条小径弯弯曲曲穿过,铺了碎瓷砖,立了石凳石椅,还立了两盏灯,但也没什么人来,左右都是房屋,看不到海,吹不到风,太阳都难晒到。不久,移来一块大石,立在空地边,慢慢有了人,他们坐在石凳上聊天,吃东西,有时站在石头边,摆出各种姿势照相,或与人视频。
石头上刻着四个红底楷书,“洞背公园”。逛空地让我们显得很无聊,但逛公园不会,这是休闲。它大约有一百多平米,或许是地球最小的公园。
4
有人问,蛋蛋啊,我很想知道你有过几个男朋友。
我知道我看起来像有过很多男朋友的人,像那种时刻在奔跑的人,一边追逐人,一边甩掉人。
我问,怎么界定是男朋友?亲过的就算,有人迅速给出标准。二十几个人每人两只眼睛,连一只正在吃鱼的猫都抬起头看我,我说,“亲哪里才算?”
5
世界从来不给真相,就像七月暴雨如注,雨以最大的力量从天空一跳而下,溪水发出一年里最大的轰鸣声。团团乌云接踵而至的傍晚,突然有一团乌云没接上,山峦上方露出窄窄一线蓝得发黑的天空,半满的月亮投下温柔而慈爱的光。
我将双脚伸开,单车以比车还快的速度冲往桥,冲完桥再推到村口,一连冲了三次,直到乌云把月亮完全遮住,但那一晚,以及后来乌黑暴雨的几天,我心里都有月光。
八月之舞
1
植物越过绿的巅峰,果荚裂开,种子垂直插入泥土,没结果的也不再生长,雨也不再下,这一年剩下的时间,秋天用来枯萎,好躲避冬天的狂风。
日子一个接一个,同样的时刻发生同样的事情。早上九点,我醒来,缓缓走出梦,开始同样的一天,不阅读,不说话,频频起身找东西吃,各种欲望拧成食欲,只有食欲是我可以即时满足的。
2
某些夜里,梦允许我走进它。
浮在海上看到虾,走到田里看到鱼,穿过菜畦看到果实累累。我两手空空地往深处走,睁开眼看到黎明。
如果能合并梦,我一定双手捧虾,将鱼绑在身上,蔬果绑成一捆,一路踢回家。这叫大丰收。
3
只要在深夜漆黑的天台上走几圈,将目光投到山和海面的隐约的船只上,就会发现这里和几年前一样,草替代了草,树替代了树。
我在这里曾对生活抱以极大希望,将失去的和不曾拥有的,一一寻补: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共枕的恋人。每个新的日子里,每个小时的流逝里,我对自己说,给点耐心,那些精神和肉体的愉悦一定会到来,你,还有时间。
4
过了八月,我的身体和植物一样悄悄越过巅峰,枯萎有助于躲避冬日狂风,一只不请自来的猫,是屋子里唯一增添的东西。
我将它的到来解释为馈赠,除了它,世间万物都不需要我的注视。
九月,从一天到另一天
1
有一扇朝北的窗的人,要比有一扇朝南的窗的人,提早十天得到秋天。天气总有办法弥补,北窗的春天也迟来十天。
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南北窗,理论上,可以将喜欢的季节延长或缩短。但很少人会察觉。拥有很多的人对季节往往会迟钝一些。
2
北面的山上,风等了两个季节。一声令下,风擦着山坡各种植物而下,裹着芳香和暗语齐抵窗口。
风瞬间鼓满屋子,窗帘、挂着的锅铲、猫身上软软的毛、未绑起的头发,以及光着的腿,都摇晃起来。

3
二楼的出门,灯彻夜开着,她在的时候也是这样。她觉得猫在夜里喜欢玩,不喜欢睡。五楼的去二楼喂猫,喂完后把她的灯关了,他觉得猫白天黑夜都想好好睡觉,和他一样。
4
我的猫要麻烦很多。
夜里,除非将它留在家里,否则要走远很难,它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到开关院门的声音,还没下坡,“咚咚——咚”,它奔跑,肉垫子踏路的声音。它会确认你是否看到它,看到了,它就藏在路旁的车底下或草丛,悄隐着身子与你保持平行,去哪跟到哪。
离住处稍远,或遇到狗它不敢往前时,它会向你发出巨大的哀嚎声,交集着控诉、悲痛、狡猾与召唤。
对动物的辜负比对人更容易背上一生,我奶奶当年从草尾搬到岳阳时,她养的黑狗跟着船在沅江边跑到天黑看不清,一边跑一边叫,这叫声到奶奶的晚年还在回荡。
猫跟着我时,我从来走不远,就在村口附近走走,它像我的小小影子,跟着来来回回。
5
高速上,内侧一条路封着,这几天在修剪植物。
昨天两辆车闪着灯停在内侧,二三十米远,几个人有蹲有站地围着,围着一团火,地上放着几摞纸钱,这匪夷所思的地方,可能就是往生地吧。
6
七月半了,这几年她们烧纸的时候都没跟我说,之前说的时候她们能感觉到我忘记这件事了,我确实忘记了。
前天晚上做梦,母亲倾其所有在其他城市买了一套房子。她中断以前的生活,到新城市里辛苦地生活着,只为了住在自己的房子里。
如果真有七月半,她应该收到钱了,并已买好了房子。
7
没有必要事情做的日子,像无穷无尽的早上、中午和晚上以及深夜不间断的连接。
生活单调得像停止了,或死在原地,这时,等了两季的风从北面的山上冲下来,清凉,天真而无畏,就像是我和虚无单调之间的一种缓和。
从一天到另一天,会发现只有单调才能穿越单调,得到欢娱。
十月风大,从此少去处
前天晚上回来时,我开得很慢,接近溪涌时,路的弯道特别美,我曾多次在这里感受到油然的幸福。现在,我看着弯道、山、黑暗里隐约的海,等着熟悉的安宁感重新到来。它没有来,惆怅与沮丧还在我体内,迟迟不肯撤退。
一直到拐进山,进门,拧开灯,几天前我离开时的生活原封不动显现。我走进去,就像水走进水,好了。
前几天我在龙华,清理掉屋里别人的生活痕迹后,明知只待几天,我还是买了锅、酱油、油、菜。从背包拿出衣服,挂在衣柜里。
锅用过一次后,以前的生活咚咚跑回来。我记得阳台上每一株半死不活的植物是如何买或偷来的,记得夏天夜里坐在阳台拣来的矮石块上吃饭喝茶,彻夜失眠时,坐在秋千上荡到晨光如拉开帘幕一样突然明亮。
这里有了新城市的气质,建筑很新,绿植每隔几年就换,人群永恒年轻,二三十岁,他们白天以秒计实现各种价值,夜里交欢但不繁衍。
我很想对她说,你跑到那人迹罕至的地方,一待待几年,你疯了,你得到了什么?脸色蜡黄、一只猫、一天里除了训猫没有人和你说一句话,你写了吗读了吗?你的眼睛马上就无法在夜里看清任何一行字了但你还没有爱人,如果这是你要的,你疯了,如果不是但却不得不这样,你也疯了。
我看到镜子里的她忍不住同情又愤怒,而为了消除愤怒,我骑着单车四处转,感觉这个原来熟悉的地方,现在变得危险、热情、冷漠而焦灼。
两种生活差异巨大,任何一种只要离开都休想再撬开,休想重新开始,你,已经失去这个城了。我在夜晚的城市游荡,经过一对对情侣或快成情侣的人,他们是获得爱的人。我一生羡慕那些获得了爱的人,在我不太多的爱情经验里,只有极少时刻爱是对等的。
大多时候,我都处在一种不可获得的感伤里,或是掉头离开的怅然里。
对物的眷恋要纯粹很多,我住过的地方,只要建立过正常的生活秩序,一旦打破都会让人感伤,哪怕我的物品只剩下一点点,它们藏在柜子里或塞在床下,但只要它们在,我仍然将这里当成我的一个去处。

最后一个下午,我拖干净客厅和房间,用手机拍下我以后有可能会翻出来看的相片,拿了一把刀,两个碟子,喝了一半的牛奶,两个鸡蛋,半袋枣和排插,这是我在这个屋里最后的东西,拿走它们,这里不再与我有关。
我用力抬了一下门把手,钥匙往左转动一圈再抽出来。我希望电梯来得慢一些。
回村路上遇到十月的第一场风暴,雨大如水帘,我开得慢,路面的雨像擦地跑的云一样。我想,回到村后,先把猫找到,抱着它回家。我还要告诉它,从此,我只有这一个去处了,离群索居,但我们不怕,你有我我有你,我们雨大关门,风大关窗。
十一月不急,一步步来
1
村前的建筑物慢慢脱下编织网,一天天露出白色的外墙和玻璃窗,它们毫无特色,不能用美丑评述,它挡住了我们眺望过的海。月亮不再从海面升起,它从建筑物的屋顶升起。
三年前,这些建筑群的地方是连绵的山,山上成片的荔枝林与大叶相思树,山谷长满芦苇,冬天清晨的浓雾停在芦苇丛里久久不散,把村子一整面山隐藏起来。
2
十一月过半,我忘记了这一年我是怎么过的,好像过去为这新来的十一月腾出了地方。我对十一月满怀希望,关于健身、看书、写字以及治疗头疼都有崭新的展望,并打消想买电视的念头,离脱贫还很远,应该省点电费。
今年只剩下很少时间,气候学上的冬天早已到来,真正的冬天也会在这个周末全速压境。蔷薇苟延残喘,它被我种到风口,一年要吹掉好几次叶,不开花是对的,这个阳台不配有任何努力开出的花。
我的植物现在终于明白,除了水,我什么也没有给它们。我一天无数次起身去看它们,指望它们自己从秋天里获得,并成熟。
3
我也不指望从其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杠铃让我的腰紧实了而臀部翘了,猫是知道的,但它只想看见鸡肉。明年我开始处理身体以外的东西,比如头脑或灵魂(如果有这样东西的话),我将拥有以前没有的智识,想对以前说爱我的人说,请收回你们短暂而不结实的爱。
我的脖子挺得直直的,仿佛仅仅是想象,就已获得智识与勇气。
总之,我不急,一步步来,万物拥有同样的时间。
十二月只有一天
朋友带来三张木刻的年历,每一张都有十二个小方块形,嵌进日期。我想这三张够我用很多年了。
我要买胶,把它们贴在墙上,让我的每一天都呈现在这三张纸内,这是我的时间地图。只要我走近年历,它就能准确无误地指出我在哪一个日期里。
年历不会偏袒,未来和过去一样多,均匀分布画面,庄严静谧。
我瞬间有了秩序感,将年历摆在地毯上,等有胶了,我还要贴几张海报。海报也是朋友拿过来的,快三年了一直放在书架的顶上,我很喜欢它们。
仅仅是想象年历和电影海报将出现在墙上,我就已经获得对抗阴冷一天的力量了。我跪在地毯上,手肘搁在沙发上,翻开早上从卧室带出来的书,塞林格的《九故事》,打算仔细读一篇。
书页泛黄,几年前买回来时曾抱着虚荣和看看到底牛在哪的心态翻过,但每一篇都半途而废,仅有的印象是枯燥,永远都不想翻开。仅仅是因为知道它是好东西而没有丢掉——我的大部分书都是这样幸存下来的。现在重新翻开读,并不是计划,纯粹是顺手,站起来,右手一抬,是书架第一格的位置,刚好它薄,就取了下来。
书前几天就抽出来了,当时看了三四篇,前两篇还好,看到意料之外的好,正暗喜阅读能力有了进步,碰到《与爱斯基摩人开战前》,完蛋。看是看完了,但不知它说了些什么,不知作者为什么要写个这么寡淡的东西,无聊无用无趣,且对话啰哩啰唆。
我感到的不是挫败,而是一种被欺凌。我将书甩到一边,开始玩猫,给它开一只罐头,分三天给,它拱起背重重地擦我的腿,昂起头看着喵喵叫。
现在我跪在地毯上,双肘搁在沙发上,打开书,重启信心。翻到困难页,看了两页,突然想起什么,转身爬到年历旁看小方块,每个小方块的缺口,朝着不同的方向,那是每个月的周末。赫然想起不同年份的周末都不一样,所以,年历无法重复使用,它的有效期只有一年。
我的宏伟计划——三张年历用一生,彻底落空。
我直起身,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书也不看了,坐在沙发上,重新审视我的猫,它带给我的乐趣,值不值得我买罐头。
本文摘编自

《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
作者: 周慧 著 / 黄灿然 选编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艺文志eons
出版年: 202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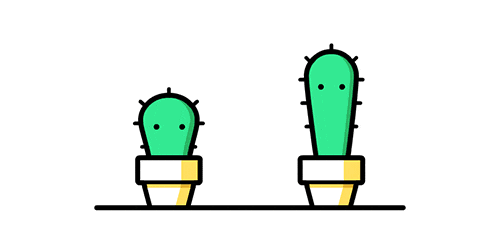
编辑 | 串串
主编 | 魏冰心
配图 | 《四个春天》
知识 | 思想 凤 凰 读 书 文学 | 趣味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