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定陶便是菏泽吗 , 星期天文学·孙一圣

周五好,这里是「星期天文学」。也许有读者还记得这个名字,它初创于2016年,是凤凰网读书最早的文学专栏之一。这几年,我们与网络环境相伴共生,有感于其自由开放,也意识到文字载体的不易,和文学共同体的珍稀。
接下来的日子里,「星期天文学」将以一种“细水长流”的方式,为纯文学爱好者设宴。这里推荐的小说家,年轻而富有才华,是新文学的旗手,他们持续而毫不功利的写作,值得我们多花一点时间,也补缀、延展了我们的时间。
「星期天文学」第33辑,嘉宾是作家孙一圣。《全家福》是孙一圣的最新作品,通过一个几乎是一天之内发生的故事,拼贴出一个家庭的聚散。书中没有离奇的情节和宏大的叙事,就像作者说的那样,有时候,苦难仅仅意味着“平凡”地“活着”。
故事从老师要求上交一张一寸照片讲起,大人们眼中不重要的照片,在孩子心中有不同的分量。下文节选自《全家福》,在寻常的一天,一个寻常的农村小孩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向城市进发……

孙一圣,1985 年生,山东菏泽曹县人。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天南》《青年文学》等杂志 。曾获得“2015 年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 ”。出版小说集《你家有龙多少回》《夜游神》、长篇小说《必见辽阔之地 》。
全家福(节选)
我知不道该到哪里去。
上到坡顶,便是两头都通的柏油路。紧紧傍着柏油路的河岸也向两头无情延伸。柏油路好宽,柏油路也好远,远到两头都使不上劲。
我跑在柏油路上,知不道到了哪里,只能看到前方晃晃悠悠的路面,发着白光。超过我的三轮车和自行车赌气似的一下子没了踪影。
这条路有一段弯来弯去。这些弯路,远远看去,弯曲得可厉害了,待我跑近,弯曲又奇迹般挺直起来。
我走在路边,几番机动车的声响远远传来,我转身拦车,没人停下。走到一个陌生的路口,我终是拦住一辆载满棉花的机动三轮车。司机其次才是个司机,他首先是个农民,与爸爸妈妈一样。这个农民没有熄火,在隆隆的声响里,大声地问我,你去哪哈儿?我说,到菏泽。农民说,我不到菏泽。随即,似乎是可怜我,农民说,怎么就你自个儿,你爹娘呢?我说,我就是到菏泽去找他们。农民说,那你上来吧,我只能拉你到定陶,我就到定陶,过了定陶你要自己过去了。
驾驶座只能坐下一个农民。我抓住紧巴巴的麻绳,爬到车斗后面高高的棉花上。抓结实喽,农民头也没回地说。而后,他启动三轮车,开了出去。我的身体朝后仰了一仰,叫我看到蔚蓝的天空和棉花一样的白云。我努着劲俯身下来,紧紧地抓住比棍子还硬却弯曲的麻绳。
三轮车开得稳当,架不住柏油路蹦蹦跳跳,我坐在棉花上面也跟着跃跃欲试,牙齿咯咯打架。坐久了,我便觉着自己也是棉花了,不过,我是实心棉花。坐在高处,我看到前方的道路不但蜿蜒曲折,也高高低低。开始的道路我还知道,这里去过,那里走过,后面便什么也知不道了。两边的平原,也紧张兮兮地抖动,说不定哪里很不自在地胀出一个坟包,很快便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了。
三轮车的蹦蹦跳跳更多了。我又仰脸看到天上一团一团的白云,似乎一动不动。如果农民拉的是一车打包的白云,我便是坐在一团一团的白云之上,蹦蹦跳跳了。
拐到更大的柏油路,三轮车又跑了好大一阵,不时有货车呼啸着超过我们。我更加知道这是大大的柏油路了,比我见过的所有道路都宽。
农民在一个很像路口的路口停下,这个路口与其他路口也很像。我从上面秃噜下来。农民告诉我,往前不远,便是定陶了,我不能再走了。他与我摆摆手,便隆隆开车走了。他刚刚下到土路,车后簇起一阵烟尘。
这个下午出奇地安静,阳光也好得过分。我跑了一阵,两旁的平原没有动静。我再跑一阵,知不道到没到定陶,平原看起来毫无变化。下了柏油路,拐进东面的小路,有个人的影子出人意料地跑到我前面,几乎要贴地飞翔了。不用猜,那一直是我的影子。

穿过一片杨树林,我莫名来到铁轨边上。现在我知不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因为火车道有两个方向,哪一个方向都能走出这里。我小心地踩在枕木上,跳着走,不时掉下来,踩到碎石上。走不多久,便看到一个卖冰棍的女人。
她是那样肥胖,也不骑车,就推着自行车,走在铁路边上。她自行车后座载着的白色泡沫箱子灰不拉叽,不太干净了。箱子里面定然裹着两层厚厚的棉被。这样的箱子,里面通常装的都是冰棍。每次看到卖冰棍的,我总奇怪,棉被能够保温,裹得越严实越暖和。为什么用棉被把冰棍裹了起码两层,没把冰棍焐化,反是越焐越冷呢?这个问题总叫我想不通。
她走路也不快,却很快超越我了。走不上几步,她便停了下来,不多会儿,她又走动起来。她走走停停,像是故意等我。等我走到她边上,她亲切地问我:小朋友要不要吃冰棍?我也不做声,只是摇摇头。她有些顽固,再次问我,一个人跑到这哈儿干么子呢,荒郊野地的。
我乜她一眼,习惯性地摇摇头。我的意思是,我不去哪哈儿。而后继续走。我看了看她,以为我说出了这句话,没意识到我没说出来。
她说,小朋友,你家哪哈儿的?
我说,平原的。
她说,哪的平原?
我说,太平的平原。
她说,太平离这好远,你怎么来的?
我走在一根一根枕木上,严格说,我的步子没有那样大,我是跳过一根一根枕木。每跳向下一根枕木,我便鼓起足够的勇气。我再次鼓足勇气说,走来的。
不要走在铁路里,她说。
我看了看遥远的铁轨,非常直的铁轨,没有一处弯曲,几乎是漂浮在平原之上。我依旧走在铁轨里。我期待有火车开来,哪头开来都好。
她说,你这是要去哪哈儿?她等了一会儿,说,是要回太平吗?
起初,我没注意,待她顿了一下,慢吞吞说出后半句,我才想到她是怕后半句惹我生气才说得小心。我好像知道她的想法了。因为怕我生气,她可能在猜,猜我离家出走。她的后半句不是问句,而是劝我回家。我说,我不回家。
她说,小朋友知道这是哪哈儿吗?
我的抗拒心理有些缓解,甚至有些心急地问道,哪哈儿?
她说,这是屠头岭。
我说,屠头岭不是在定陶吗?
她说,屠头岭也是曹县,不是定陶。屠头岭在定陶边上,你再往前走便到定陶了。
我说,过了定陶便是菏泽吗?
她说,过了定陶便是菏泽。
我突然激动起来,说话也不自觉大声了。我飞快地问她,连我自己也没听清,她却听见了。我问:那是不是快到菏泽了?
她说,到菏泽还早呢,还有好远。
我泄了气似的,双腿发酸,几乎软下去,要倒掉了。我尽力撑住,沮丧到绝望地问道,那有多远?
她说,你问菏泽做么子?
我说,没么子,随便问问。我怕说错话,就再不说一句。
我闷葫芦一个,又走了一阵,突然跳过下一根枕木,双脚齐齐落在石子里头。我踩着碎石,继续闷头走。我几乎没有力气,也没有勇气了,我不再计较是否每一步都踩中枕木,而是走在石子里,枕木反倒成了我的阻碍。走不上两步,便遇到一根碍事的枕木。我开始讨厌起枕木来了。
不要走在铁路里,她又说了一遍,待会火车来了。
我抬头看看,两头都没有火车要来的迹象。我期待的火车像是不来了。只有火车道接力一样从远方一截一截传过来。无论哪一截火车道都比火车快许多,也漫长许多。

因此,我没有听她的话,我走我的,她走她的。我不明白,她的步子为么子总是迁就我。她再次主动与我搭茬:小朋友知道屠头岭,很厉害哟。
我说,我有个姑姑就在屠头岭。
她明显地兴奋起来,眼睛也变得明亮,说,你姑姑叫啥?
我说,知不道。
她说,那是你姑姑唉,怎么能知不道。
我说,知不道。就听我爹讲过一次,说是屠头岭有个姑姑。我没见过我姑姑。我说话的口气,好像整个屠头岭没有别人,只有姑姑一个人。
她说,你爹叫么子?
我说,赵立人。
不待一会儿,她说,你姑姑叫赵立萍吗?
我被问住了。我的两只手知不道该放哪哈儿,也知不道姑姑该不该叫赵立萍。我便弯下腰,捡起一颗石子,紧紧攥住。攥得手疼了,就尽力扔得很远很远。其实,扔不了多远,我听到石子蹦了两下便没有声音了。我分辨出第一下石子沉闷地撞在了石子堆里,第二下石子清脆地撞在了铁轨上,第三下什么声音也没有,应该没入草丛了吧。我找不见石子扔到哪哈儿去了。于是我说,知不道,没听我爹说起过。
我跳上了铁路右边的单条铁轨,支开双臂,以防失去平衡。我小心翼翼地走着,故意放慢脚步,好叫这个女人尽快超过我,离我越来越远。很可惜,她始终与我并肩走,为此,她付出了比我更慢的努力。我们相安无事地走了一阵,我不慎滑落了一只脚。我的身子也趔趄了一下。她责备地说,我说不叫你走铁路吧。我没理她,尽力把脚下两边当作万丈悬崖,掉下去我便拍扁了。这样的想法,更叫我摇摇晃晃了。我终是失败了,一只脚崴进石子堆里。
这里的石子那样多,总有一颗石子是崴进姥爷鞋子里的石子吧。
她突然说,小朋友你一个人在这里太危险了,跟我回去吧,去你姑姑家。
我看了看她,迷惑地说,你认得我姑姑?
她睁大了眼睛,说,何止认得,我便是你姑姑啊。
我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说,你真是我姑姑?
她说,对啊,我就是你如假包换的姑姑。
我说,你有么子证据,证明你是我姑姑?
她说,我是赵立萍,你爸爸不是叫赵立人吗?如果你爸爸是平原的赵立人,我就是你姑姑。
我还是不信,我说,怎么能这样巧,这样巧碰见姑姑。
她说,你要不信,跟我去屠头岭,到了姑姑家里,你就知道了。
我居然心动了,我说,真的吗,你真是我姑姑吗?
她说,跟我走吧,到姑姑家去。
怎么会有这样巧的事,真叫人惊讶。随便走个地方也能遇到姑姑,好像天上掉下个姑姑来帮我。这叫我想起爸爸老说的话,“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天意不用来下雨,竟用来下了个姑姑。姥爷知道了,又该担心了。我比姥爷更担心,担心她不是姑姑,抬头看到她走得远了些,我几步追上来,又开始轻信她是我的姑姑了。
我不自觉地跟在姑姑后头,控制不住地慌张,紧张到手心冒汗。我怕她真是姑姑大过怕她是骗子,也从没想过她是骗子的后果。没走多远,姑姑突然转过的脸惊动了我。我与姑姑隔得不是很近,也远不到哪里去,是那种我们刚好是姑侄的距离,没有亲密无间,又有血缘拉扯。
就这般走着,我们两个人都是,没有刻意接近,也没有离开更远。仿佛她不是我姑姑了,而我也忘了她是我姑姑。在离我俩都不远的地方,就在她脑后的上方,应该是气球飘浮的位置,飘浮着一个姑姑,由她牵住,也供我瞻仰。
她终于想了起来,隔着不远的距离突然停住,从自行车后座四四方方的泡沫箱里,拿出一根冰棍,递给我。
她说,吃冰棍吧。
我眼睁睁看着,没有伸手去接。她几乎要塞我手里了,说,吃吧吃吧。
我想吃,甚至不自觉咽了一口唾沫。我还是没有接。
姑姑说,拿着快拿着,再不吃就化了。
我慌乱地低头,也不走了,脚尖顶着脚尖。
姑姑说,不吃吗?不吃我放回去了。
她明明是吓唬我,待我抬起头,却真就放回去了。我心内反而后悔起来,几次想开口要,终究没敢说。我甚至主动下了火车道,跟在姑姑后面,再次后悔刚刚没接冰棍。
我们走了许久,有火车开过来。火车来晚了,晚到根本担负不起姑姑警告的危险。火车也没有太晚,至少还能致以晚点的恭喜,恭喜我找到了姑姑。
早在走上火车道之前,我便看到了那柱大烟囱。那柱烟囱是那样巨大,无论我走多远,走多近,那柱烟囱终是那样巨大。并且无论从四面八方哪个地方都能望见那柱毫不费劲的烟囱。
累了吧,马上便到了,姑姑亲切地说。姑姑指着不远处高耸入云的烟囱说,喏,看到那个烟囱了吧,就在那里,很快便到了。姑姑开了话匣子,也不问我意见,自顾自说,本来我从没想过要卖冰棍,一天也卖不了多少。你看到那个烟囱了吧,那个烟囱便是烧砖的窑厂,我原来是窑厂的。没想到吧,一个妇女也能去窑厂烧砖,那也确实好累。屠头岭的窑厂你听过吗,应该听过的,没听过也没关系。我是我们厂里干活儿最卖力的,我们工资计件,拓坯、晾晒我都在行。烧制就不归我了。烧砖是个技术活,火大了火小了都不管。烧老了,烧成琉璃了,这一锅便烧坏了。所以,我只能拓坯了。拓坯也要技术呢。当年窑上还办比赛,那个热闹嗬。也不是窑上不要我了,就是不能烧砖了。谁知道呢,就是不让烧砖了。说是土地资源浪费,挖土太多了,就不让烧砖了。你说谁家盖房不用砖,不烧砖用么子盖房呢。谁能想到土也是一种资源,跟煤和石油一样了。这样一来,我便无事可干了。窑厂都倒了,去哪哈儿干呢。窑厂倒都倒了,烟囱还杵在哪哈儿,跟个大傻子似的,你说好笑不好笑。

这是一个没有外人的地方,外墙便是红砖砌就(存心与姑姑作对似的),铁锈的大门吱呀发抖。铁门大开,好像等我许久了。姑姑仿佛专门捡了这样一个瘆人的院落,一进门便见到许多纸扎。纸马、纸屋、纸人、纸轿子,各色各样,应有尽有。这是一处纸扎铺。姑姑要买纸扎吗?
开始还好,进了门才觉察到,空气里满是腥味。院子内墙布满青苔,搁着地排车的下盘,那便是车轮。进到屋里,堂屋正中靠墙的条案摆着木牌灵位,一鼎小香炉,两只供碗,碗里盛着水。不远处,多出了一张桌子,也多一把椅子。这是一把奇怪的椅子,与我等高。转角走过去,索性看到一个孩子,慢慢向我走来,走到不能再走了,我俩只好脚抵脚头碰头了,我贸然喊了一声,声音低在肩膀以下。这个对面抵住我的孩子只是我,我终于看见我了,有那么一瞬,我以为我是被我喊出来的。而这不过是一面镜子。
这里便是姑姑家了吧,我想。
有人吗?我以为又是我喊,我想再喊一声时,才发觉那是姑姑在喊。没人回应,穿堂风从背后吹来。
没过多久,有人从背后走来。
这是一位我从不认识的女人。看起来,她与姑姑差不多大。她那爽朗的大笑和走路的姿态,一下便区分了她与姑姑。她说,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她在努力不让自己别扭。知不道为什么,我想拔腿便逃。虽然她是与姑姑说话,看起来我不过是个透明人,她也完全看不见我,但实际上她的克制早已紧紧捉住了我。
然而,她们两个又似乎完全忘了我,因为她们尽情地寒暄,热情而浓烈,恨不能把对方的话也夺过来替她说了。我觉得她们是在比赛,比赛到底谁能撑住不闭嘴,比赛谁能比谁说得更多。
知不道过去多少辰光,她才恍然大悟一样,啊呀看我这脑子,你们渴了吧,我去倒杯水。她说话比刚刚不自觉地更大声了一些。
我在躲女人,也在躲姑姑,因此,意外撞了一下椅子,我也躲起椅子了,然后,我再次看到那个孩子了。这是个有些脏乱的孩子,头发蓬乱,褂子和裤子都垮垮的,鞋子也脏。与刚刚一样,有那么一瞬间,我没想起这个孩子就是我。几乎同时,我也再次没想起这里还有个镜子呀。
姑姑忙忙说:“啊, 不用了不用了,我今次来……”一把拽我过来,与她耳语几句。女人听着,偶尔瞟我一眼。
我紧张起来,有种想喊妈妈的冲动。起初我知不道为什么想喊妈妈,过后许久,我才明白我应该想喊救命,因为情况紧急弄错了。
女人毫不知情,俯身过来。她在随意弯曲,明明只有肥胖的腰肢在弯曲(她并不肥胖,只有腰肢肥胖),她的随意却显得她哪哪都在弯曲。叫我站在那里,无辜得像一根干柴。
女人问,你叫么子名字?
我说了。
女人问,你爸爸叫么子?
我说,赵立人。
女人扭头看看姑姑,说,这便是了。女人扭头与我说,我的小哎,我是你姑姑呢。
我大为惊讶,不得不去看她身后的姑姑。姑姑却鼓励地点点头,我有些不知所措,惊慌地说,你不是我姑姑,我姑姑叫赵立萍。
女人道,对嘛,我便是赵立萍。
我再次望向站在后面的姑姑,向她求助。第一个姑姑说,傻孩子,这才是你姑姑。我要是不诓你说我是你姑姑,你怎么肯与我来?
那第一个姑姑把我留在了姑姑家里,便先自走了。她走了许久,我再次环顾一周这个家,和这个家的物什、家具。这个家委实有些太大了,我心生惧意。不过家具都很旧,是用久了那种旧,跟房子长在一块儿了。那个姑姑走了许久,久到我再也不想想她了,可我仍然忍不住想她,想她也应该是这个房子的一件家具,因为我仍然觉着那人是我姑姑,眼前的赵立萍则是假姑姑。而这个家则不然,我已先入为主地认为这是姑姑家。我深深觉着赵立萍与这个姑姑家是如此的不和谐,与堂屋墙壁和家具统统闹僵了,比我还要别扭。

想到此,我警惕起来,觉着我被姑姑拐卖了,觉着赵立萍不但是假姑姑,甚至是人贩子。我茫然四顾,却也不敢表现出这份忧惧。于是当赵立萍唤我名字时,我忍不住一阵哆嗦,喏喏应声。
赵立萍道,你去铁路那边做么子?
我本想胡乱支应,支吾半晌,遭不住说了实话,我要去菏泽。说出口以后,很骄傲似的,好像菏泽就是北京,就是那个很大很大的地方。
赵立萍说,去菏泽做么子?
我说,去找爸爸妈妈。
赵立萍说,你爸爸妈妈不在家吗?
我不吭气,不是我不想说,实在是知不道该怎么答。
赵立萍终于想起她是大人了,担负起姑姑的责任道,不要老想玩,老想跑到城里去玩。城里有么子好玩,不是楼房便是汽车,没个站的地方。你这样乱跑,跑丢了可咋办嘞。
我委屈巴巴地说,我没有。然而,我没有意识到,从这一句开始,我内心深处竟然不自觉地承认她是我姑姑了。
赵立萍说,你没有……怎么跑到这哈儿来了?
那天下午,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一转眼,我再次看见院子里的纸扎,纸马、纸屋、纸人、纸轿子一字排开。而姑姑不是窑工吗,姑姑为么子要扎纸扎?我到现在也还没法转过这个弯,甚至把我弯到岔路,觉着世上所有房子都是纸做的,人马车轿也是纸做的。
这要是个纸做的世界该多好。
姑父从院子里走进来,我有些恍然,以为是那其中一个纸人经了阳光一照,闪了一闪,排开众纸扎,走了过来,进到堂屋里。姑父敞着怀,赤着两只脚,一只裤腿挽到膝盖,另一只裤腿挽在脚脖,已是湿了。湿掉的那条腿有些瘸(好像湿掉的纸腿来不及变成姑父便走过来了),不是很明显地一拐一拐。姑父刚刚进来,赵立萍便问姑父,你脚怎么了?姑父说,摔了一跤,不打紧。赵立萍待要发作,姑父抢先看见我,便说,这是哪家的小孩,像个呆瓜。赵立萍登时嗔怒,说么子呢!
他们问我饿不饿。我没有说话。他们认为我不好意思,便认定我饿了。他们应该早已吃过午饭,但晚饭还要等好久,又怕我饿着,临时做了一餐饭。他们劝我多吃。我不饿,几乎一口没吃,只眼睁睁瞪住一盘炒螺蛳。赵立萍看在眼里,说,你要吃这个吗?这是你姑父下午搁河里刚捞的,趁热吃。说着她便将盘子移到我面前。我纳闷说,河里不是没水吗?姑父说,你不懂了,没了水才好捞螺蛳,都搁淤泥里窝着呢。我想吃螺蛳,又不敢吃螺蛳。姑父不由分说,硬给我吃。我拗不过,硬着头皮嘬了一个。吃时我还安慰自己,就吃一个,也就一个,应该没事吧。我怕吃螺蛳吃到头霍然掉了。
老早时候,听爸爸讲,从前有个小孩螺蛳吃多了,因为螺蛳里有寄生虫,堵在喉咙下不去,再以后,不管这人吃么子都饿,因为吃进嘴里的东西都被这寄生虫吃掉了。时候一长,寄生虫连脖梗子也蛀空了,他就变作瘦巴巴一个,整日顶着硕大的脑颅,摇来摇去。不一日,他不听话,他爸生气打他一耳刮子,他的头霍然就掉了。
赵立萍问我,你跑恁远找你爸妈干么子?
我嚼着螺蛳,本来想说照片的事体,但是,只吃一个也吃得嘴上挂油,我怕说的话出溜滑倒,更是麻烦,左右解释不清楚,于是我说,交学费。
赵立萍说,你学费没交吗?
我点点头,没有吭气。
赵立萍说,你学费多少?
我说,还差二十。
赵立萍低下头不说话了,隔了许久,才道,快点吃,吃完早些回家。
我想说,我不回家,我要去菏泽。但我没有说出口,菏泽卡在喉咙没有说出口。菏泽和刚刚咽下的螺蛳一同卡在喉咙了。
是啊,我不能永远住在姑姑家。我知道我要走,知不道什么时候该走。我没觉着我要走,却被赵立萍在门口捉住。我重新回到堂屋许久了,有那么一瞬间我疑惑我在哪里,我先是认为我抢了椅子的位置,接着我想我是一把椅子。我的迟钝,让我慢慢意识到只是椅子蔓延到我身上来,并且将我淹没。我完全没有想过,我不过是坐在椅子上。
赵立萍平白抱来许多衣裳。赵立萍说,这都是你表哥的衣裳,他都穿不住了。赵立萍不由分说拉开我的书包,我被吓住了。赵立萍以为我嫌弃,解释说,都是洗干净叠放起来的,现在看还像新衣裳。我没料到会莫名其妙多出一个表哥。我怀疑赵立萍为把这些不要的衣裳硬塞给我临时编造了一个来历不明的表哥。赵立萍牢牢拉住我,简直像是提溜起了我。赵立萍从后背不停地往我身体里塞衣裳。这些衣裳一股脑挂在我的后背,很重很重,好像我是个驼背。我的书包就是这时,出其不意从我的后背变了出来。
先前我从学校出来,一直背着书包没有放下。鼓鼓囊囊的书包,挂在我的后背,除却很重,也突然慎重起来了。
赵立萍领我走进一条昏暗的小胡同,两旁的墙壁因为有树,显得格外的斑驳,映着遥远的犬吠,直至胡同的尽头。翻过篱笆,来到村里的前街,一路走去,在第一个十字街口左转,我再次看见那柱巨大的烟囱了,好像是那柱烟囱帮我们转到了左边的街道。现在我有种错觉,这个巨人一般的烟囱就在姑姑家,然而我在姑姑家非但没有见过这个烟囱,甚至在姑姑家的时候把烟囱忘了个一干二净。我这个傻子。
走不上几分钟,赵立萍率先扎进荒草丛生的树林,树下那些胡乱开着的红色或者白色的小花一脚便能踩碎了。穿过这片树林,赵立萍与我来到高人一等的柏油路边。
柏油路总是弯曲的,柏油路不是从路的尽头出现的,而是从弯曲里拐出来的。

可见事情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才叫我与姑姑先自看到他们。
道路尽头,突然冒出一群人,几乎是村里的人全都来了,挤挤挨挨。男人的叫声、妇人的骂声、孩子的哭声,无不响彻天际。
待到他们来到近前,姑姑拉了我一退再退。在他们后头便是好些神仙。可以说我先自望见了他们。他们个头高高,边跳舞边向前走,一刻也不停歇。神仙老爷踩着高跷,几乎没有身子,只是戴着巨大的面具。那面具五颜六色,泾渭分明。有些神仙我不认得,是那长胡子和大红脸还有身着破旧衣裳的和尚(摇着开裂的蒲葵扇);我最认得的是唐三藏、孙悟空和猪八戒,我只纳闷为何没有沙和尚;再往后认出一个铁拐李,我便知道这一群是八仙过海了(我数不过来有没有八个,他们便跑过去了)。他们后面便是呼儿嗨呦的许多汉子,足有七八个,赤膊拉纤,后头便是一只大船。船头有男孩女孩高高举了柳枝,船尾也有男孩女孩把柳枝压在后头。汉子们喊了几阵号子,“呼儿嗨呦”,便是喊:“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我看到大船在柏油路上拖行,行得很慢,也摇摇晃晃,便是有水从船里泼洒出来。原来船里盛了水的,船舱里则碧波荡漾,涛声阵阵,犹似装了一瓢大海,泼洒了一路。
这场游荡,浩浩荡荡闯了过去,我和姑姑像是洪水过境后的石头,突兀地冒了出来。姑姑离我有八辈子之远了,看见我后慢慢走了过来。我问姑姑,那是什么,是游神吗?姑姑安慰我似的说,我们叫它“旱地行船”,求雨用的,天光大旱才有这等热闹。
原来这样远的定陶也与我们一样干旱啊。
犹如蝗虫过境,路上留下深深的痕迹,我好奇那只大船怎么没把柏油路搅烂了。
他们从定陶而来,可能蹚过曹县,向着巨野去了。然而,我总觉着他们是从姥爷那儿来的,尽管,姥爷是在他们过来的反方向。
机动车很久不来了,好像都被大船轧扁了。好容易来一辆,也晃晃悠悠。尤其这辆拖拉机,突然从路面冒了上来。眼看拖拉机愈来愈近,慢到几乎要停住了,并且真的停在我们边上了。拖拉机后面的车斗里升起一位姑父。
我不得不怀疑拖拉机司机和姑父是前面那场游神队伍落下的两个懒汉。
姑父跳下车,与赵立萍使眼色,邀功一样朝拖拉机努努嘴。怪不得姑父早早不见踪影,原来找拖拉机去了。
赵立萍抱我上了拖拉机的车斗,让我坐在空旷的车斗里。我本以为赵立萍要与我一块儿,原来姑父只是找来一个要路过太平镇的司机顺路捎我回去。
临走,赵立萍背过身去,从里面的衣服兜里摸出一块叠了几叠的方帕,再从裹在橡皮筋的纸币里分出两枚一块钱的硬币交给我。赵立萍交了硬币到我手里,看了我一眼,眉头一皱,又从没有裹起的方帕里挑出了一枚硬币,再次交到我的同样一只手里。拖拉机的突突声里我分辨出了清脆的钱币声。赵立萍说,拿着,到家买点好吃的,穷家富路的,莫嫌少。到家好好听爸爸妈妈的话,不要再乱跑了。赵立萍说罢再次叮嘱司机一定要把我送到太平镇上。
拖拉机走远了。赵立萍和姑父的腰背竟然佝偻起来。他们两个摇摇手,应该看不见拖拉机了,才掉身回去。他们需要穿过树林,走过漫长的街道,越走越慢,好像耗尽了一天的力气。如果我跟他们回去,也一定会跟着他们转进胡同。姑父走路也不一瘸一拐了,先是进了院门,穿过院中众多的纸扎才能进到堂屋。赵立萍刚刚进到院门,抬头看见姑父走进纸扎堆里,再也没出来。
赵立萍晃神的一瞬,姑父瘦成一张纸片了。赵立萍你有没有想过呀,姑父竟然是这样瘦巴巴的一个人呀。
本文摘选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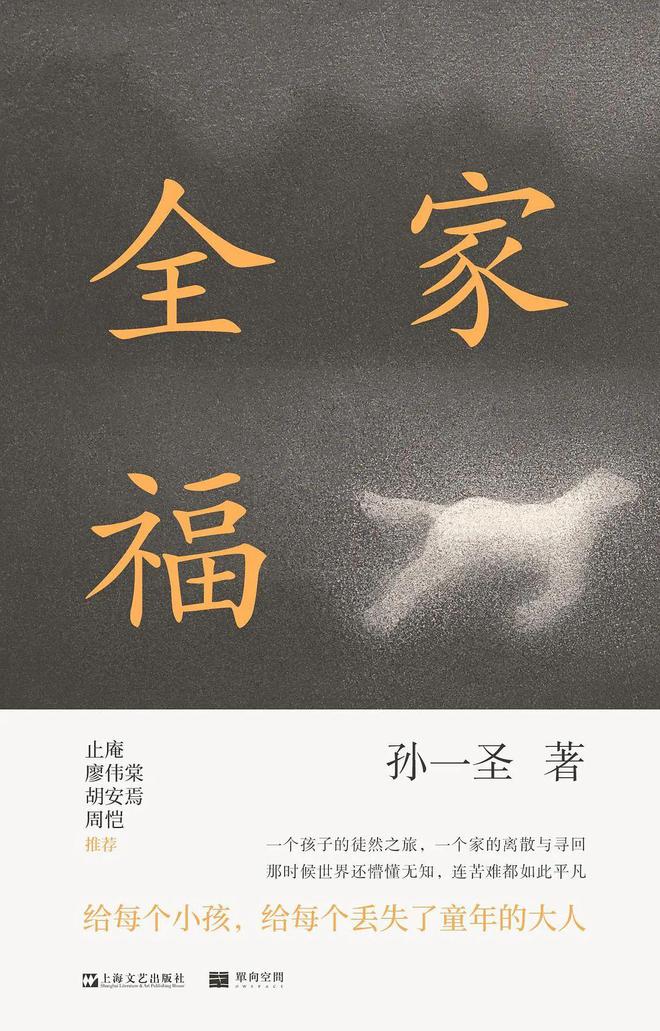
《全家福》
作者:孙一圣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铸刻文化/单读
出版年:20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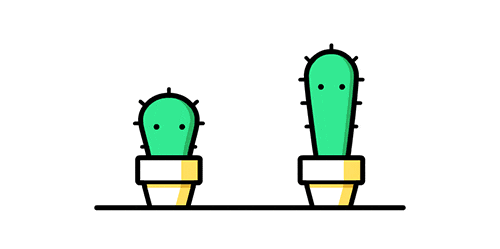
编辑 | 刘洁
主编 | 魏冰心
图源 |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鲭鱼罐头》
知识 | 思想 凤 凰 读 书 文学 | 趣味
网友评论